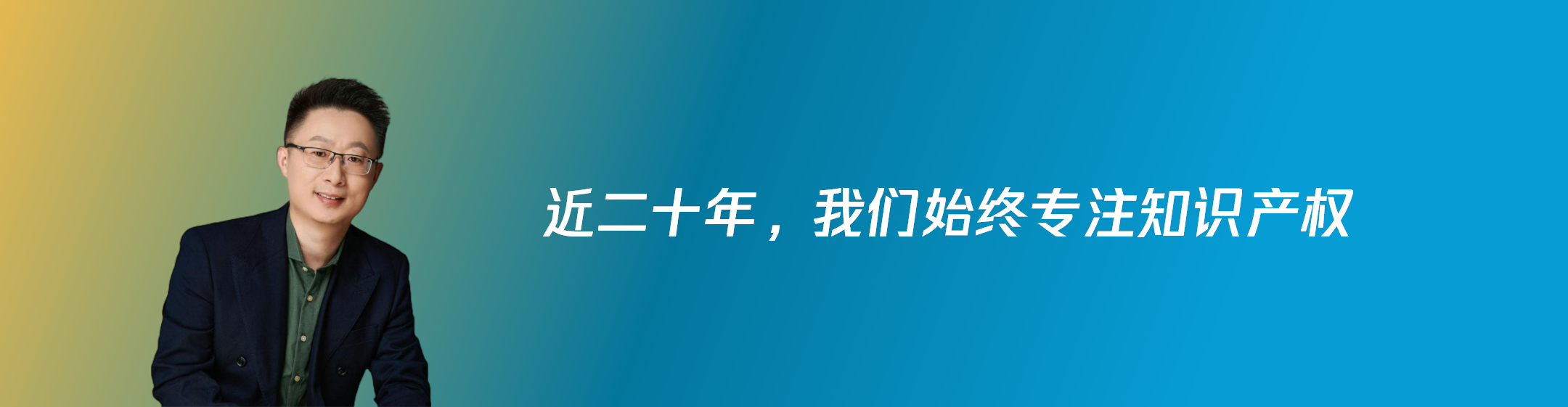作者 | 宋建立 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教授,法学博士
作者 | 宋建立 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教授,法学博士
摘要:从早期TRIPs协议对商业秘密民事侵权的规制到晚近CPTPP对民事和刑事责任的规范,凸显了国际社会从严惩治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共识。商业秘密法律制度在我国有一个认知、借鉴和不断完善的过程。近些年商业秘密案件数量不断增长与案件疑难复杂性趋强,司法实务面临挑战,如存在将违反保密义务型侵权简单等同于不正当获取型侵权行为的现象,模糊了不同侵权行为的性质及侵权人主观恶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事案件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和刑事案件对损失数额计算方式。本文针对一些特殊情形的侵权行为,分析研究了对于常见的员工带离商业秘密行为的责任承担,应考量其后续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做到“过罚”相当;对于技术秘密许可类案件,保密期限届满并不必然影响保密义务终止;员工离职后保密期限应具有合理性,避免限制员工的职业选择和发展;商业秘密侵权行为推定规则的适用,应处理好证明程度和证明标准的问题,防止推定规则的滥用;商业秘密侵权抗辩事由的适用标准等,以期助益商业秘密执法和司法实践。
关键词:商业秘密;侵权行为;行为类型;行为性质;法律责任
商业秘密在现代企业竞争中的地位愈加重要。从全球范围看,商业秘密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各国越来越重视商业秘密在促进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商业秘密保护已成为参与全球贸易的制度共识和门槛,且日益受到关注。在对外关系中,中美经贸谈判有关商业秘密民事和刑事保护的内容成为知识产权领域一项核心议题,并成为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中首要磋商解决的问题。“在许多大型公司,据估计商业秘密成了其2/3的无形资产。即使在最小的公司,他们也许也都拥有商业秘密,即使也许他们并不知道。”[1]可见,商业秘密不仅仅是企业自身的资产,更是国家经济安全与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近年来,无论商业秘密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数量均呈现增长趋势,刑事案件数量增幅较大。国内外经营者对于完善商业秘密制度和惩治侵害商业秘密行为的呼声高涨,商业秘密保护也已成为当下中国经济生活和创新发展的重要议题。
一、商业秘密侵权规制国际趋势与我国立法演变
国际范围内对商业秘密保护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WTO项下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属于较早将商业秘密纳入保护范围的国际公约。TRIPs协议第39条正文率先引入“未披露信息”,并对披露信息的侵权行为作出规定:
“自然人和法人应能够防止其合法控制的信息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以违反诚实商业惯例的方式向他人披露、获取或使用,只要此类信息:(a) 属于秘密,即其整体或其组成部分的精确配置和组合不为通常处理此类信息的相关领域内人士所普遍知晓或易于获取;(b) 由于属于秘密而具有商业价值;并且(c) 合法控制该信息的人根据情况已采取合理措施对其进行保密。”[2]
为更好理解条文中“以违反诚实商业惯例的方式向他人披露、获取或使用”的涵义,特别以注释10作出阐释:
“就本条款而言,‘违反诚实商业惯例的方式’至少应指违反合同、违反保密和引诱违约等行为,包括第三方在明知或因严重疏忽而未能知道涉及此类行为的情况下获取未披露的信息。”[3]
又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第18.78条系商业秘密保护专条,该条正文概括描述了商业秘密侵权行为:
“在保证有效防止如《巴黎公约》第 10 条之二中所规定的不正当竞争的过程中,每一缔约方应保证个人有法律手段以阻止其合法控制的商业秘密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以违反诚信商业惯例的方式向他人(包括国有企业)披露、被他人获得或使用。”[4]
但对于何谓“违反诚信商业惯例的方式”,专门以注释137作出解释:
“就本款而言,‘违反诚信商业惯例的方式’至少指违反合同、泄露机密和引诱违约等惯例,并包括第三方在获得未披露信息时知道或因重大过失不知道获得过程涉及前述惯例。”[5]
该条还特别对商业秘密刑事犯罪行为方式作出例举:
“每一缔约方应对下列一项或多项行为规定刑事程序和处罚:
(a) 未经授权且蓄意获取计算机系统中的商业秘密;
(b) 未经授权且蓄意盗用商业秘密,包括通过计算机系统的方式盗取;或
(c) 欺诈性披露,或作为替代,未经授权且蓄意披露商业秘密,包括通过计算机系统的方式披露。”[6]
由此,CPTPP成为首个要求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进行刑事规制的国际性贸易协定。TRIPs协议与CPTPP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的手段与方式并无实质区别,基本可为划分为不正当手段型和违反保密义务型。
TRIPs协议谈判过程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最终通过的文本,对各国制定有关商业秘密保护法律规范起到重要示范效应。商业秘密在国内被确立为一个重要的法律概念,是在1991年4月9日修订并施行的《民事诉讼法》第66条[7]和第122条第2款的规定,[8]这是我国法律首次使用商业秘密的概念。由于诉讼法系程序性法律,故未对商业秘密的内涵作出明确规定。商业秘密概念的出现,既是借鉴了TRIP协议早期谈判成果,更是基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1992年1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签订《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其中第4条规定:
“为确保根据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十条之二的规定有效防止不正当竞争,中国政府将制止他人未经商业秘密所有人同意以违反诚实商业惯例的方式披露、获得或使用商业秘密,包括第三方知道或理应知道其获得这种信息的过程中有此种行为的情况下获得、适用或披露商业秘密。”[9]
中美有关知识产权谈判所达成的协定或文件对推动商业秘密法律制度具体化起到积极作用。
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秘密的概念、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类型均作出规定。至此,我国竞争法意义上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正式确立,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类型也以法律形式予以明确。[10]为细化上述法律规定,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5年颁布了《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与《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相比,没有根本变化,但《若干规定》第3条第1款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关于“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规定,细化为第1款中的两项:即:
“三、与权利人有业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违反合同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四、权利人的职工违反合同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明确了职工及有关单位和个人属于负有保密义务和保密要求的主体范围。这种重大明确规定,实质澄清了对职工能否成为侵权主体的疑虑,重申了立法本意是将职工作为商业秘密的侵权主体。[11]这主要是考虑到职工与所在企业的特殊关系,职工侵犯商业秘密的案件多发,是侵犯商业秘密的主要情形,如果不纳入商业秘密侵权的主体范围,显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重要缺失。
2017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对侵权商业秘密的行为方式作出进一步完善:一是新增“贿赂、欺诈”为获取商业秘密的手段,与原规定的“盗窃、胁迫”一并列举为侵犯商业秘密的手段,原有的“利诱”则被“贿赂”所替代;二是完善了“视为侵犯商业秘密”规定,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第三人以非法目的向知悉商业秘密的“员工、前员工或者其他单位、个人”获取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该第三人行为被视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2019年《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商业秘密侵权行为作出重大修订:一是纳入新型侵权手段。此次修订将通过电子侵入方式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与传统方式非法获取商业秘密的手段“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等一并列举为侵犯商业秘密的一种手段。主要考虑到随着互联网发展,利用黑客技术获取他人商业秘密正成为主要方式,因而修订时增加规定通过电子侵入方式获取他人商业秘密也属于侵权行为;二是规定了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第9条第1款第4项增加了教唆、引诱、帮助他人侵权的规定,即教唆、引诱、帮助他人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商业秘密的行为,被纳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范围。
2025年修订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2025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规定了有关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内容,基本保留了2019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的内容。
综上,商业秘密法律制度在我国有一个认知、借鉴与不断完善的过程,这是我国加入WTO履行国际义务和扩大开放融入世界经济的实际需要。我国商业秘密保护与国际规则的接轨,亦会成为未来加入CPTPP的现实考量因素。因此,商业秘密侵权行为作为重要的侵权构成要件,研究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类型及性质,对于厘清不同类型侵权行为社会危害性以及确定损失计算数额,对于商业秘密犯罪构成要件的判断均有实质意义。[12]
二、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类型及特征
2025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1款第1-3项列举的三类经营者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其分类主要依据侵害行为的性质,即第1项规定的是不正当获取商业秘密行为,是依据获取手段的非法性进行定性的;第2项是第1项的递进性规定,即对于不正当获取的商业秘密再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行为;第3项规定的是与前两项规定无关的、独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即违反保密义务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行为,掌握商业秘密本身是合法的,只是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而对其掌握的商业秘密进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构成第3项规定的侵权行为的前提是存在保密义务,而保密义务产生于保密协议和保密要求。第9条第2、3款则规定了视为侵犯商业秘密的情形。
第10条对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形态作了穷尽式列举性规定,实际划定了商业秘密保护范围,即对其保护范围采取了行为类型法定原则。之所以采取类型法定原则,主要基于行为类型法定意味着以限定行为类型的方式限定商业秘密权利的保护范围,即法定范围以外的行为即使具有侵害性,也不宜再以《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规定的一般条款给予补充保护。[13]在广州市艺哈贸易有限公司、胥某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中,[14]原告主张,被告以在原告的工作微信上删除涉案客户信息的方式窃取其商业秘密。法院判决认为,反不正竞争法所规定的“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行为”是以盗窃、贿赂、电子侵入等积极方式不正当地获取他人商业秘密,从而不正当地获得竞争优势的行为,而不包括以删除等消极形式的损毁、删除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因此,仅有删除行为本身不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年,作者注)第九条第一项所规定的“以不正当手段获取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
(一)直接侵权行为与间接侵权行为
以经营者是否直接实施商业秘密的获取、使用与披露行为为标准,可分为直接侵权行为与间接侵权行为。
1.直接侵权行为。2025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1款第1项规定了不正当获取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属于一种以积极方式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独立行为。即以“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构成侵权,是否披露、使用在所不问,亦不影响违法性的认定。以商业秘密来源是否正当,可将直接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划分为不正当获取型和违反保密义务型。
(1)不正当获取型。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将不正当获取商业秘密的手段分为常发生的不正当手段和其他不正当手段两种情形。该行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商业秘密来源是否系通过非法手段获取。
常发生的不正当手段如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所规定的“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实践中如:
“包括高新聘请‘挖人才’获取商业秘密,也包括重金收买,诱使企业技术人员披露商业秘密等情况”。[15]
“派出商业间谍盗窃权利人的商业秘密,通过侵入权利人电脑系统盗窃权利人的商业秘密,通过提供财物、高新聘请、人身威胁、制造把柄等方式诱惑、骗取、胁迫权利人的员工为其获取商业秘密等。”[16]
这是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起草者和2017年修订者对于不正当手段的解读。竞争法意义上的盗窃,一般是指行为人采取不易为权利人察觉的方式,秘密地将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置于自己管控之下。行为人对商业秘密的窃取,可以有多种情形,如将载有商业秘密的文件等偷偷据为己有;复制后还回原件、保留复制件;以电子数据形式转移信息;将商业秘密的内容通过大脑“记忆”下来,置于自身控制之下等等。由于商业秘密本身所具有的无形性,使得盗窃商业秘密与盗窃有体物有所不同,特别是“记忆”商业秘密后置于自身控制之下,则为传统盗窃方式所不具有,不能用有体物占有转移的标准去判断属于无形利益的转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规定对“盗窃”规定为:
“采取非法复制等方式获取商业秘密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盗窃’”。
此定义着重强调了未经授权以复制等方式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仍侧重于载有秘密信息的有体物的转移,难以涵盖秘密信息无形转移的情形,如仅凭“记忆”获取商业秘密后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的行为。竞争法意义上的贿赂一般指以给付物质利益或者其他利益的方式诱使他人告知其商业秘密的行为。这种行为特征系以许诺利益诱使他人泄露商业秘密。贿赂作为一种不正当谋取交易机会或竞争优势的行为,不仅挤占了商业秘密权利人原有的市场份额,扭曲了市场竞争机制,对正当竞争行为的腐蚀效应明显,为各国法律所禁止。竞争法意义上的胁迫是指以损害他人财产或者人身为要挟,迫使他人告知其商业秘密,包括对知道商业秘密者的胁迫以及与知道商业秘密者有关系的亲属等其他人的要挟,此种行为往往以“恐吓或威胁”等方式施加精神控制迫使他人交出商业秘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规定:
“未经授权或者超越授权使用计算机信息系统等方式获取商业秘密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第 一款第一项规定的‘电子入侵’”。
“电子入侵”能否成为与“盗窃、贿赂、欺诈、胁迫”并列的侵权方式,并列列举是否合理值得研究。因为,“电子入侵”通常属于窃取商业秘密的具体行为手段,如以复制还是“电子入侵”方式,故“电子入侵”不应成为与盗窃并列的手段,立法将其并列规定似欠缺严谨性。但这种并列规定满足了实用主义的需要,逻辑时常会服从实用。[17]
其他不正当手段,是指与盗窃、贿赂、胁迫在行为性质及后果上相当的非法获取权利人商业秘密的手段,因无法纳入列举性手段的情形,故立法将列举性规定以外的侵权手段纳入“其他不正当手段”。“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手段难以穷尽列举,因此以‘其他手段’兜底。”[18]例如,知道知悉商业秘密的人有酒后乱言的习惯,故意设计将其灌醉,使其醉酒后说出商业秘密。但是,雇员由于自吹自擂或自己醉酒后吐露商业秘密,不属于不正当手段。[1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商业秘密司法解释》)第8条将“其他不正当手段”规定为“被诉侵权行为以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公认的商业道德的方式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20]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公认的商业道德”引发争议。这个规定源自《民法典》第86条和2019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的原则精神,但这两个法律条款分别规定为“应当遵守商业道德”和“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而“商业道德”的外延明显大于“公认的商业道德”,[21]《商业秘密司法解释》对此作限缩解释,与立法本意不尽一致。
(2)违反保密义务型。该行为特征是商业秘密来源正当却因违反保密义务而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是否具备保密义务系判断保密义务型侵权行为成立的前提。2019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第1款第3项将2017年《反不正当竞争法》同条款规定的“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修改为“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也就是将“违反约定”修改为“违反保密义务”,而保留了“违反权利人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此种修订旨在解决违反法定保密义务时的责任追究问题。保密义务不仅包括当事人通过合同约定的保密义务、单方的保密要求,还包括法律规定的保密义务。如《民法典》第501条规定:
“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或者其他应当保密的信息,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或者信息,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民法典》第509条[22]和第558条[23]也都涉及保密义务的规定。
作为产生保密义务的保密要求,并不是简单的单方行为,而是在保密义务基础法律关系存在的前提下,成为保密义务的依据。就产生保密义务而言,首先,被要求保密的信息必须是商业秘密,即具有秘密性的信息。其次,在没有保密协议或保密条款的情形下,员工或者其他人员是在权利人提出保密要求的前提下被告知商业秘密,即员工或者其他人是在承担保密义务的前提下知悉商业秘密。虽然保密要求是权利人的单方行为,但这种行为基于权利人与被要求保密者之间具有劳动合同等基础法律关系,使得单方保密要求具有了合理性。倘若仅具有劳动合同等基础法律关系,权利人并未向员工或前员工等提出保密要求或者无证据证明其提出过保密要求,员工亦不会因信息具有秘密性而产生保密义务。
《商业秘密司法解释》第10条第1款和第2款对当事人保密义务作出规定,该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实际是一种默示保密义务:
“当事人未在合同中约定保密义务,但根据诚信原则以及合同的性质、目的、缔约过程、交易习惯等,被诉侵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获取的信息属于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人对其获取的商业秘密承担保密义务。”
如何认定默示保密义务是商业秘密保护中的难点。与明示保密义务不同,默示保密义务的适用需要考量个案具体情形,但因缺乏明确法律规定易引发滥用。若默示保密义务泛化适用,最根本的影响是对商业秘密所有者利益的过度保护。[24]因此,默示保密义务的适用前提是当事人之间存在特殊的信任关系,而这种信任关系使商业秘密权利人能够披露商业秘密,并且对方知道或应当知道商业秘密的存在。信任关系作为保护商业秘密的基础,一般指不论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只要因具有信任关系而知悉商业秘密,就负有保密义务。[25]多数普通法的判例系基于信任关系保护商业秘密。与普通法国家不同,默示保密义务在我国法律适用属于例外,只有严格限定适用原则与范围,才能平衡好权利人与相对方之间的利益关系,这对裁判者而言无疑是个考验。
2.间接侵权行为。简言之,就是直接侵权的教唆与帮助行为。2025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1款第4项规定了间接侵权行为,即:
“教唆、引诱、帮助他人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从上述规定看出,教唆、引诱、帮助者只是辅助他人实施,而非直接实施侵权行为者,构成教唆、引诱、帮助行为的前提是实施者须负有保守商业秘密的义务。但是,对于教唆、引诱、帮助实施上述法律第10条第1、2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即教唆、引诱、帮助他人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立法并未作出明确规定。此类行为是否亦构成间接侵权,实践中颇有争议。从法律解释原则看,既然法律仅就教唆、引诱、帮助实施第10条第1款第3项侵权行为作出规定,也就排除了教唆、引诱、帮助实施第10条第1、2项的侵权行为,未将教唆、引诱、帮助实施第10条第1款第1、2项的情形纳入侵权行为,并不违背解释原则。那么,教唆、引诱、帮助实施第10条第1款第1、2项规定的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是否构成民事侵权,从权利保护的必要性、惩治行为危害性以及类似情形类似处理考量,本文倾向于将这些行为依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规定,如《民法典》第1169条规定的教唆、帮助侵权予以处理。[26]即教唆、引诱、帮助他人以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或者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获取的商业秘密,构成教唆、帮助侵权行为。当然,前述行为构成民事侵权的情形下,自然也应受到相应行政法规的约束,成为行政执法的对象。
(二)非经营者侵权行为与第三人侵权行为
以经营者之外的行为主体是否实施了2025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的获取、披露和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作为依据,可分为非经营者侵权行为和第三人侵权行为。非经营者侵权行为与第三人侵权行为属于上述法律第10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的两类视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二者虽然在行为主体的范围上并无差异即经营者以外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均可成为侵权主体,但根本区别在于,非经营者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自身实施了第10条第1款规定的情形,而第三人侵权行为系行为人并不直接实施第10条第1款规定的情形,而是明知或应知他人实施第10条第1款规定的行为并获取商业秘密后,仍获取、披露和使用的该商业秘密的行为。
非经营者侵权行为,在法律上被视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系相对于经营者侵权而言的。竞争法意义上的经营者是指从事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27]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法律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则构成不正当竞争。2025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1款对经营者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作出了明确列举,即非法获取行为;非法获取后的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行为;违反保密义务行为;教唆、引诱、帮助行为。非经营者侵权主要以经营者之外的主体身份作为认定依据。2025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2款将此类行为主体实施的行为视为侵犯商业秘密的情形,即:
“经营者以外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实施前款所列违法行为的,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也就是说,只要经营者之外的主体实施了2025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的情形,可以被视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可见,经营者侵权与非经营者侵权,二者除主体身份有明显区别外,在侵权实施方式和手段上并无差别,均包括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
第三人侵权行为规定于2025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3款,即:
“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员工、前员工或者其他单位、个人实施本条第一款所列违反行为,仍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该商业秘密的,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竞争法意义上的第三人侵权行为,是指第三人明知或应知商业秘密的来源不合法,仍然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其行为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三人并不参与实施2025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的行为,而是在他人非法获取商业秘密后,第三人在应知或明知的状态下仍然实施获取、披露、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法律除将具有竞争关系的市场主体作为侵犯商业秘密的主体外,亦将具有上述情形的第三人视为侵犯商业秘密的主体,实际扩大了侵犯商业秘密的主体范围。需要注意是,第10条第2款规定的“经营者以外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是否包括第10条第3款规定的“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员工、前员工”,即“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员工、前员工”是否属于第10条第2款规定的视为侵犯商业秘密的主体,仍要从对市场竞争的影响角度,区分不同情形加以考虑。“如果员工、前员工违法获取商业秘密,或者违反保守商业秘密的约定,自己将商业秘密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员工、前员工自己就成为‘经营者’,构成对商业秘密权利人的不正当竞争,可以适用本条第1款的规定”[28]从立法者上述解释看,若“员工、前员工”将商业秘密用于自己组织或参与的生产经营活动,则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经营者”,应纳入第10条第1款规定的侵权主体;若“员工、前员工”并未自己生产经营含有商业秘密的产品,只是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则落入第10条第2款规定的视为侵犯商业秘密的主体范围。从侵权行为类型看,视为侵犯商业商业秘密的行为类型,仍分别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的商业秘密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行为,行为类型并未扩大。
三、特殊情形下商业秘密侵权行为及责任认定
行为及其方式不仅能反映社会危害程度,亦能反映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行为性质的认定影响违法性判断及赔偿数额计算。特别是在刑事司法中,不同行为类型造成损失数额的认定方式不同,直接影响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定罪处罚。故准确认定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类型是定罪量刑的前提和基础。下面,对实践中容易产生争议的若干特殊侵权情形作一分析。
1.公司员工带离秘密信息行为定性与责任
实践中,商业秘密纠纷大多因员工或员工离职而引发,员工或前员工是侵权的主要主体,占比80%以上。[29]涉密员工违反单位保密义务,通过复印、拷贝、拍照、私发个人邮箱等方式将秘密信息带离单位,使秘密信息脱离单位控制。就员工而言,获取秘密信息后通常有两种情形:一是将秘密信息自我留存,不作他用,二是将秘密信息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从司法实务看,单纯获取商业秘密不是获取人的根本目的,多数是为进一步披露或使用作准备。但是,公司员工合法知悉和掌握商业秘密,违反保密义务将商业秘密带离单位置于自身控制之下,是否构成2025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不正当获取行为,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一些裁判认为,此类“带离”情形构成不正当获取行为。例如,在洛阳瑞昌石油化工设备有限公司与程某侵犯商业秘密案中,涉及员工程某将公司商业秘密转发至个人邮箱的行为构成对公司商业秘密的侵犯。法院判决认为:
“程某违反所签保密协议的明确约定,非为瑞昌公司利益和使用目的,以不正当手段擅自复制、拷贝瑞昌公司的商业秘密文件,构成对瑞昌公司商业秘密的侵犯。”[30]
在大连倍通数据平台管理中心与崔某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中,最高法院判决认为,员工崔某作为涉密人员违反保密义务,将涉密信息通过邮件发送至私人邮箱,该行为致使涉密信息脱离原单位控制,致使涉密信息存在可能被披露和使用的风险,该行为构成以盗窃手段获取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虽然崔某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年,作者注)第9条第1款规定的经营者,但根据该法第9条第2款的规定,崔某的行为应视为实施了第9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盗窃权利人商业秘密的行为。[31]
按照上述判决观点,如果行为人在未经技术秘密权利人许可,以复印、照相、发送邮件等方式窃取权利人的技术秘密,使得该技术秘密脱离权利人的原始控制,则行为人构成以不正当手段如盗窃获取他人商业秘密。行为人在实施窃取权利人技术秘密之前是否合法知悉该技术秘密,对盗窃的定性不产生影响。
有裁判则认为,此类“带离”情形难以认定为违反法律或者公认的商业道德的不正当获取行为。在北京能量盒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量盒公司)与曹某及志爱之陆(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侵害技术秘密纠纷一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曹某作为能量盒公司的技术人员,有权限接触、获得技术秘密,并无证据显示其获取商业秘密的手段是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入侵。作为能量盒公司的技术人员,尽管存在将工作中接触到技术秘密带离办公场所、转移至非办公电脑的行为,但难以认定上述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公认的商业道德,不能归入《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年,作者注)第9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行为类型。[32]
按照上述观点,2025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1款第1项不适用合法知悉商业秘密的行为人,即因岗位职责合法知悉商业秘密的人,即使违反义务要求将商业秘密以发送电子邮件、存入私人电脑等方式“带离”单位,亦不属于该项规范的范围。由于“合法获取”与“不正当获取”是两个互为排斥的概念,已经合法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人不可能同时构成非法获取。故凡是具有合法接触并知悉商业秘密的主体,均不宜被认定为“不正当获取”进而适用2025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1款第1项。
对于公司员工带离秘密信息行为的定性,上述裁判观点截然不同,各有其道理。本文认为,商业秘密作为极具核心竞争力的秘密信息,公司通常将存放场所、存储载体和应用场景进行严格限制,目的在于保障秘密信息安全与防止泄密风险。若公司员工因岗位职责便利将秘密信息带离单位,使秘密信息以不为人知的方式脱离单位而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员工违反保密义务的行为构成民事违法并无不妥,若从广义法律意义上将此种行为理解为“盗窃”亦无不当。且由于民事赔偿固有的“填平”原则,究竟是以不正当手段还是以违反保密义务的方式获取商业秘密,对损失数额认定并无实质影响。但若考虑适用惩罚性赔偿时,以不正当手段积极主动的获取行为与违反保密义务的违规披露使用行为相比,行为人主观恶意程度还有差异的,这将影响到应否适用惩罚性赔偿以及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因此,在商业秘密民事案件中,还是应秉持侵权行为定性的严谨性,避免不区分情形简单归入不正当获取的范围。
在刑事司法中,辨析商业秘密获取方式则直接关系“损失数额”认定,而“损失数额”是判断商业秘密犯罪构成要件“情节轻重”的关键要素,决定着应否追诉与刑罚轻重问题。如,天津知识产权法庭审理的赵某侵犯商业秘密罪一案,该案被告人赵某原系艾曲西公司销售部员工,其在该公司工作期间,私自将大量公司文件存储于配发的移动硬盘内,并在离职后带离公司。法院以合理许可费确定损失数额,认定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此案被称为全国首例以合理许可费确定损失数额的案件。[33]显然,此案将该员工带离秘密信息归入到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商业秘密的行为。
员工带离商业秘密,公司作为商业秘密权利人要求追究员工侵犯商业秘密罪刑事责任,该如何认定带离行为性质并按何种方式计算损失数额。若将员工带离行为一律解释为“盗窃”或“不正当行为”,那么,司法解释中关于违反保密义务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时,损失数额按照销售利润损失确定的规定,将被架空而失去规范意义。先前司法解释起草者亦认为:
“认定‘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前提是,行为人此前并不掌握、知悉或者持有该项商业秘密,以区别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违约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行为人合法正当获取商业秘密后违反保密义务侵犯商业秘密,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行为,而不属于该条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例如,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员工参与了商业秘密研发或者因日常工作使用而知悉该项商业秘密,获取行为是合法正当的,其违反保密协议擅自复制商业秘密的行为,不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不正当手段’的情形。”[34]
固然,出于保护创新和维护竞争秩序目的,给予商业秘密权利人必要保护当属必要,但若保护过度,如刑罚过于严厉,将产生限制市场竞争、员工自由流动等违背法治基本原则的效果。[35]因此,商业秘密刑事案件涉及公民人身自由,在适用法律时应当秉持罪刑法定原则,任意扩大解释将可能导致“入罪”标准降低,产生商业秘密过度保护的副作用。对于员工带离商业秘密的行为,应区分情形分别对待:(1)员工带离商业秘密但尚未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情形。不论员工基于何种目的利用工作之便将商业秘密带离单位,此情形下,尽管员工违反保密义务,但其并未造成现实的经济损失及严重社会危害性,是否具有刑罚上的可责性值得研究。因为刑罚惩治的是犯罪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这是与一般违法行为的根本区别。在并未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性情况下,仅凭“带离”行为本身也难以准确认定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在美国法中公司员工违反公司保密规定将秘密信息存入个人电脑,虽然构成商业秘密侵占,但因无实际损失而无须赔偿。美国伯克利大学法学院普利(Pooley)教授通过判例讲述,此类行为构成商业秘密侵占,但一般只给予权利人禁令救济,因无实际损失而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即便要赔偿,至多也只给付1美元这样的名义损害赔偿。而且,此类行为几乎不太可能构成犯罪,因为很难证明其犯罪故意,陪审团也不会支持有罪认定。[36]同样的行为在中国法下,不仅因违反保密义务而承担违约责任,而且依相关司法解释规定需承担刑事责任。在未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后果的情形下,追究刑事责任似有违刑法的谦抑性。(2)员工带离商业秘密后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情形。此种情形属于公司员工违反保密义务的披露使用行为,而非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不正当获取行为。依照司法解释精神,违反保密义务的披露使用行为造成的损失数额应根据商业秘密权利人的销售利润损失而非商业秘密许可费用确定。实践中确有将此种情形下损失数额以许可使用费计算的现象。许可使用费的确定大多模拟许可条件和许可使用的场景,类比相类似专利技术的许可费用进行资产评估,其中对损失评估方法和评估因素的选取,往往成为损失数额评估的难题,且许可条件模拟设置缺乏合理性与科学性,加之当前无形资产评估领域不甚规范,许可费用评估虚高往往成为质疑焦点。虚高的评估结论更易成为入罪和刑罚制裁的理由,这也凸显了辨析员工带离商业秘密行为的性质对于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重要性。
2.侵权产品的销售行为与“使用”商业秘密行为
2025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1款第2项禁止“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行为。该条中商业秘密的“使用”是指未经权利人许可将商业秘密运用于产品设计、产品制造、市场营销及其改进工作、研究分析等经营活动的行为,即自己直接利用商业秘密使用价值的行为。允许他人使用是指商业秘密获取人将商业秘密提供给第三人使用的行为。商业秘密的使用形态多样,《商业秘密司法解释》第9条将其概括为三类:一是在生产、经营等活动中直接使用商业秘密,如使用构成商业秘密的配方、方法、工艺,直接用于制造同样的产品。二是在商业秘密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改进后再进行使用,如对属于商业秘密的配方进行改进后,制造特定的产品。在被诉侵权人进一步修改、改进商业秘密后再行使用的情形,在比对时并不要求其所使用的信息与商业秘密实质相同。三是根据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相应调整、优化、改进与之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如根据权利人研发失败所形成的数据、技术资料,以及研发过程形成的阶段性成果等商业秘密,相应优化、调整研发方向;或者根据权利人的经营秘密,相应调整营销策略、价格等。[37]后两种使用方式通常被称为改进型使用和消极使用,虽然在这两种情形下,被诉侵权人在最后生产环节实际使用的信息与涉案信息会存在一定差异甚至完全不同,但其在产品设计、改进或研究分析等环节中依然使用了商业秘密,因此可能节约了研发成本或者采取了针对性策略,并据此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应当认定构成使用商业秘密。[38]
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的“使用”商业秘密是指直接将商业秘密应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之中的行为,不包括使用商业秘密生产制造侵权产品后,销售商后续销售行为及购买者的使用行为。“生产商以外的其他销售商销售侵害商业秘密的产品的行为不属于擅自使用他人的商业秘密的行为,而是在客观上构成对使用商业秘密行为的帮助,即正是基于后续的销售行为才促成使用商业秘密损害后果的发生。”[39]那么,销售侵害商业秘密侵权产品的行为是否属于“使用”商业秘密行为的帮助行为?如若一律将销售行为纳入商业秘密“使用”行为的帮助侵权之列,有扩展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非法使用商业秘密行为范围之嫌。因此,需要针对具体情形予以判断,一般而言,销售商业秘密产品的行为系同一侵权主体实施制造行为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结果,[40]将此种“销售行为”认定为非法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并无不妥。倘若后续的销售者并不知晓该商品中的商业秘密系非法获取,换言之,以合法途径购买并销售含有商业秘密信息的侵权产品,在缺乏充分证据证明销售商存在明知或应知情形时,则其销售行为则不宜归入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41]上述不知情的销售行为未被纳入商业秘密“使用”范围,表明该销售行为不属于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但并不意味着认可其市场流动的合法性,否则有损消费者合法利益。鉴于产品本身违法性的客观存在,权利人仍可以主张销售者停止销售使用含有该商业秘密的产品。
3.保密期限届满后使用商业秘密行为与责任
在技术秘密许可类协议中,当事人约定有保密期限,保密期限届满后保密义务并非相应终止。裁判规则表明,技术秘密许可合同约定的保密期限届满,除非另有明确约定,保密期限届满仅意味着被许可人的约定保密义务终止,但其仍需承担侵权法上普遍的消极不作为义务和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后合同附随保密义务。在石家庄泽兴氨基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兴公司)、河北大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晓公司)与北京君德同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德同创公司)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中,君德同创公司作为技术秘密权利人,与泽兴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和委托加工协议,明确约定泽兴公司不得外泄技术秘密,保密期限为3年。保密期限届满后,泽兴公司将技术秘密披露给第三人公司使用。二审法院认为,基于对当事人约定的真实意思的分析,在技术秘密许可合同约定的保密期限届满后,被许可人的约定保密义务终止,但其仅可以自己使用商业秘密,仍需承担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不作为义务和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的附随保密义务。[42]
与专利授权的公开、公示及保护期限有限不同,商业秘密作为非经授权程序而自产生之日起自动获得的权利,商业秘密的保护期限具有不确定性。只要商业秘密不被泄露,就一直享有法律保护,这亦与权利人选择商业秘密保护并以此长久占领市场的初衷密不可分。技术秘密许可合同约定保密期间,仅代表双方当事人在保密期间应当履行的保密义务,但保密期间届满,约定的保密义务虽然终止,但被许可人仍需承担除自己使用外的保密义务。而这种保密期限届满后仍负有的保密义务,派生于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合同附随保密义务。依据合同法一般原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都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使用;合同终止后,当事人仍应负有保密义务,否则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另外,在涉及技术秘密许可等相关协议中,保密期限届满不应解释为被许可人可以披露或允许他人使用技术秘密。因为,披露商业秘密属于放弃商业秘密民事权利的行为,放弃权利属于权利人的专有权,除非另有约定,这种权利行使不应由非权利主体即被许可人作出。
4.员工离职后保密期限合理性的认定与责任
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和商业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对员工保密义务的要求愈加严格。员工在职期间,尤其是在涉及敏感信息的职位上,通常会签订保密协议,承诺不泄露或不擅自使用企业机密。而对于离职后保密义务的保密要求与具体时限,《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对于雇佣关系终结后,保密义务人是否继续负有保密义务以及保密期限并未作出直接规定。如《劳动合同法》第23条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
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该条款规定了保密条款与竞业禁止条款,但仅规定对于竞业禁止进行限制,如给付经济补偿、限制竞业禁止的期限。如果没有给予经济补偿或者超出竞业禁止期限,劳动者就不再受竞业禁止期限的约束。但该法对于保密义务是否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继续存在未作出规定,也未规定经济补偿或者限定保密期限。原因就在于保密义务与竞业禁止的性质不同,竞业禁止主要防止员工利用在职期间获得的企业敏感信息或专业经验从事竞争性工作,而保密义务旨在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维护其市场竞争优势。一般而言,保密义务的期限会依据企业的保密内容、员工的职位以及行业特性来决定。虽然,企业对员工的保密义务有着正当的要求,但在实践中也需要关注平衡员工的择业自由,过长的保密期将限制员工的职业发展,进而影响其合法的就业权利。如何平衡员工的择业自由与企业的保密需求,是实践面临的现实问题。值得关注的是,如果商业秘密属于经营信息,或者属于创造性不高而可以成为从事同类经营活动惯常需要的技术信息,此时要求员工永久保密或者不能使用难谓公平。在当事人之间未约定离职保密期限的情形下,可以从衡量各方利益考虑,视情酌定保密期限而非一概认定为永久保密,或者在经历合理期限后认定为员工一般知识、经验或者技能的范畴而不予保护。因此,在法律框架内,合理的保密期和明确的责任划分对于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和员工的择业自由至关重要。
5.商业秘密侵权行为推定规则的适用
通常情况下,商业秘密侵权案件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推定作为一种例外情形。推定是指推测而断定,[43]是基于已知事实推论出未知事实的逻辑过程。法律上的推定是按照法律规定由已知事实推断出未知的争议事实的过程,推定行为本身实际免除了当事人的部分举证责任。[44]由于商业秘密具有无形性等特殊属性,证明被告实施侵权行为并非易事。原告通常难以举出被告获取商业秘密直接或确凿的侵权证据,因此而失去必要法律救济,对于权利人权益保障难谓公平。因此,鉴于原告举证的实际困难,从举证责任分配的角度将部分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承担,以此化解商业秘密案件办理难度,推定制度的适用就具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早期颁布的有关禁止侵犯商业秘密的《若干规定》第5条第3款规定:
“权利人能证明被申请人所使用的信息与自己的商业秘密具有一致性或者相同性,同时能证明被申请人有获取其商业秘密的条件,而被申请人不能提供或者拒不提供其所使用的信息是合法获得或者使用的证据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根据有关证据,认定被申请人有侵权行为。”
这在当时是一项极为重要的规定,为缓解商业秘密被侵权后的举证难提供了执法依据。2011年,最高法院在其司法政策中也肯定了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接触加近似减合法来源”的推定方法。[45]
实践中适用推定规则,涉及证明程度和证明标准问题,即原告提供的证据达到何种证明程度,可以推定争议事实成立。在原告举证证明被告有知悉商业秘密的条件,且能够证明被告使用的技术信息与其商业秘密相同或者实质相同,被告实施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盖然性较大,据此认定原告提供了证明侵权的优势证据,举证责任便转移为被告承担。即由被告承担其不侵权的举证责任。因为,这不是由被告证明纯粹的不侵权事实,而是通过证明其技术信息合法取得的方式,以此消解原告举证优势,如通过独立研发、反向工程、合法授权等取得商业秘密。在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吉利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诉威马汽车制造温州有限公司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一案中,[46]最高法院判决认为,对于被诉侵权人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挖取其他企业人才及技术资源, 在明显短于独立研发所需合理时间内即生产出与某项技术秘密相关的产品,其有渠道或者机会获取该项技术秘密的,因侵权可能性极大,可以减轻技术秘密权利人对于侵害技术秘密行为的证明负担,直接推定被诉侵权人实施了侵害权利人技术秘密的行为。被侵权人否认其实施侵害技术秘密行为的,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推定制度既解决了事实认定的难题,又保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平衡了原、被告之间的利益关系。如实践中处理与大脑“记忆”有关的商业秘密案件时,由于员工并没有实际复制或取走任何涉密文件或电子数据,但是员工凭借“记忆”的商业秘密的确帮助竞争对手抢占相关领域的市场,此时在权利人商业秘密与竞争对手技术信息存在相同或实质相同的情形下,适用推定规则由竞争对手就其技术信息来源作出解释就具有了合理性。在上诉人合肥搬易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陈某、吕某、潘某、苏州先锋物流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一案中,[47]最高法院判决亦认为,技术秘密相比于专利的核心区别在于其属于由权利人私力掌控且不为公众所知悉、不具有公示性的技术信息,实践中甚至不排除部分技术秘密并不体现在权利人的内部书面记载中,而仅由特定人员保存于其个人记忆中并通过技术实操示范或现场口述予以再现(例如料理食材的独门技艺)。
四、商业秘密侵权的抗辩事由
1.独立研发。随着全球经济数字化和科技创新的不断发展,商业秘密的保护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某些技术成果确实可以通过多条路径独立研发出来,且不同公司之间的技术相似性不必然意味着侵权行为。独立研发抗辩作为被诉侵权人在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常见的辩护理由之一,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该抗辩的核心是企业不通过接触他人商业秘密而获取相关信息,而是基于一般知识和技术及公开的信息进行的研发,从而主张其行为合法。然而,独立研发抗辩在法律适用中的困境也不可忽视,独立研发抗辩的有效性往往依赖于被诉侵权人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其研发的独立性,如许多高科技企业的研发过程复杂且保密性强,相关研发文档、技术资料等证据往往无法完全公开或提供。此外,研发过程中常常涉及多个环节和人员,如何在复杂的证据链中确认其独立性,成为司法机关处理此类案件面临的实际问题。
独立研发作为抗辩事由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来源于其技术成果并未通过非法手段不正当获取。主要鉴于商业秘密是通过权利人自力防护的方式而存在的权利,商业秘密不具有专有权属性且不具有强排他性,亦不排斥他人的独立研发,对于同样的信息只要不被公众所知悉,可以同时被多人分别拥有。多人拥有相同或基本相同的秘密信息,并不影响各自拥有商业秘密权利。《欧盟商业秘密保护指令》序言(16)指出:“为维护创新和促进竞争,指令对于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know-how 或者信息并不创设任何专有权利(exclusive right)。因此,独立研发同样的know-how 和信息就具有了可能性。”[48]
独立研发抗辩不仅涉及法律问题,还涉及企业间的公平竞争问题。因此,在处理此类案件时,除了要遵循法律规则,还需要考虑如何维护创新与保护之间的平衡。如果对独立研发抗辩的标准过于宽松,可能导致滥用抗辩从而损害商业秘密保护的有效性;反之,过于严苛的标准又可能限制技术创新和公平竞争。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新的技术研发模式正在改变传统的技术创新方式。机器学习等算法技术开发可能导致技术成果在短时间内快速迭代和优化,这给传统的商业秘密保护带来了挑战。因此,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法律适用中需要重点考量的问题。
实践中,独立研发抗辩通常需要考虑证明以下事实:一是证明不存在非法获取的行为。即被诉侵权人并未以不正当方式获取商业秘密或以违反保护义务、保密要求等非法方式获取商业秘密;二是证明其技术成果的创新性与独立性。被诉侵权人的研发成果并不依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而是凭借独立的技术研发实现,创新性与独立性的证明往往是独立研发抗辩中的难点,特别是在处理涉及新兴技术案件时,可以通过专家鉴定、技术对比分析等方式,科学地判断研发过程的独立性;三是证明二者之间技术相似性和差异性。尽管两者技术效果存在相似或相同,但经过独立研发,亦存在明显的技术差异,不能简单视为侵权。因此,独立研发抗辩在实际应用中仍面临较高的证明要求,同样,在判定独立研发抗辩时需要更加注重对技术差异性的审查,避免过度适用推定侵权,以更好地维护创新和公平竞争。
2.逆向工程。逆向工程一般是指对已有产品或技术进行分析,回溯其背后的设计原理及技术细节的过程,并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包括软件开发、电子产品制造、汽车工业等,特别是在一些技术更新迅速、竞争激烈的行业。逆向工程作为获取技术信息的一种手段,因其潜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不仅可以帮助了解竞争对手的技术布局,还可以通过合法手段提升自我研发能力,成为促进技术进步和推动创新的重要手段。对纠纷处理而言,亦成为商业秘密侵权诉讼程序中的一个重要抗辩事由。美国《统一商业秘密法》(Uniform Trade Secrets Act)规定的合法获取商业秘密的手段,其中包括逆向工程,即:
“从已知产品出发,反向找出其研发方法。当然,获取已知产品的手段必须是公正和诚实的,例如通过合法途径在市场上购买该产品,以使逆向工程合法”。[49]
《欧盟商业秘密保护指令》序言(16)规定:
“对合法获得的产品进行逆向工程,应认为是获取信息的合法手段,除非另有合同约定。但是,可以通过法律限制这种合同约定的自由。”[50]
《商业秘密司法解释》第14条肯定了逆向工程不构成侵权。同时,还对逆向工程进行了界定,即:
“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对从公开渠道取得的产品进行拆卸、测绘、分析等而获得该产品的有关技术信息。被诉侵权人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后,又以反向工程为由主张未侵犯商业秘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如果一家公司想要解构竞争对手的产品或者拆解每一个软件,必须谨慎地在“清白”的程序中进行,确保任何参与者都不曾受雇于竞争对手,也没有通过其他途径获取过这些信息。[51]也就是说,被实施逆向工程的产品应当是从公开渠道获取的产品,且逆向工程的实施人不能是对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的人。[52]因此,在法律框架内,逆向工程作为一种获取技术的手段,是否构成对商业秘密的侵犯,还需要具体分析。如在软件行业中,开发者通过逆向工程分析软件的源代码,在不违反使用协议或专利法的情况下,通过合法途径(如购买产品、拆解产品等)获取的技术信息,不能简单地视为商业秘密侵权。但是,逆向工程的合法性并非没有限制,其合法性前提通常是逆向工程的对象不应明确受到保密协议或有关法律保护的限制,即逆向工程也有法律边界。如德国《商业秘密保护法》亦允许实施逆向工程,但法律同时亦规定可以通过合同对逆向工程进行限制,目前在德国法中存在争议的是,权利人能否通过一般交易条款即所谓的格式合同,对其所销售的产品作此种合同限制,换言之,若以格式合同限制相对方实施逆向工程的权利,该合同条款是否会因《德国民法典》第307条第1款而无效。[53]又如,在美国法下,未经版权所有者授权的情况下,使用技术措施破解加密作品属于“规避技术措施”的违法行为,其中破解加密作品技术的逆向工程为法律所不允许。[54]同样,我国刑法第217条亦将“规避技术措施”侵害著作权的行为认定为犯罪。上述情形属于法律对某类客体明确禁止实施逆向工程。综上,利用逆向工程也应遵循相应的法律规则,避免其对商业秘密的侵犯以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确保技术创新的健康发展。
3.其他抗辩事由。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的抗辩事由往往多样化,并非所有抗辩理由都与独立研发或逆向工程相关。除了这两种常见的抗辩事由外,还有一些其他情形也可能成为被诉侵权人的有效抗辩理由,如合法公开、信息的已知性、权利转移等。合法公开必然导致秘密性丧失。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依赖于该信息具有保密性和经济价值。然而,若商业秘密在没有适当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被披露,则该信息即失去作为“商业秘密”的法律地位。[55]在许多情况下,信息的公开并非非法,而是由于其公开途径合规,导致其不再具备保密性,进而不受法律保护。信息的已知性在商业秘密保护中是判断其是否具有保护价值的关键因素。如果该信息已通过文献、专利、公开报告等方式进入公共领域,已为公众所知悉,并且能够通过合法途径轻松获取,则该信息就不再具备商业秘密的性质。信息已知性是商业秘密诉讼中的一个重要抗辩事由,常常用以证明原告主张的商业秘密在实践中已广泛被他人掌握,如某技术专利文献公开了相关的技术细节,而原告主张该技术细节为其商业秘密时,信息的已知性就成为了被诉侵权人主要抗辩理由。“权利转移”的抗辩事由,即商业秘密的合法转让。当商业秘密的所有者自愿或通过合同将其商业秘密的使用权转让给他人时,受让方在合法的范围内使用该信息不构成侵权,而是合法行使了转让方授予的使用权。[56]比如,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商业秘密转让的条款,对于抗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无论是通过并购、合作协议,还是技术授权,商业秘密的转移应通过明确的合同条款加以确认,避免后续争议。
结 语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侵权行为的方式变得更加隐蔽和复杂。传统的法律框架和司法实践已难以适应新的需求和挑战。如利用数据抓取技术从公共平台或受保护的数据库中获取大量商业信息,或者通过深度学习算法逆向推导企业技术方案,这些新型侵权方式的出现,使得商业秘密的界限变得模糊且难以追踪。商业秘密的认定不仅包括企业的核心技术、客户资料、生产工艺等传统内容,还拓展至算法模型、市场数据等在现代竞争中具有潜在战略价值的资源。同时,考虑到技术手段、市场环境、信息流通方式等多种因素,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也正从简单的“是否非法获取”转向更加综合的考量。因此,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多样化和复杂性,要求在责任认定上采取更加细致和灵活的处理方式,既要注重侵权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又要关注不同责任主体的行为模式和责任边界。
当前,尊重知识产权、尊重创新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是推动创新、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实现知识产权强国的必然要求。过去一段时间,许多中国企业走出去布局海外市场,在众多领域面对与国外同行企业的竞争与挑战,遭遇以侵犯商业秘密为由被竞争对手诉诸法律的现象并不鲜见。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数据,约有80%的商业秘密刑事案件和60%的商业秘密民事侵权案件与中国有关。[57]商业秘密不仅以其独立价值和重要性深受一些跨国公司权利人和欧美国家重视,也成为施压竞争对手的主要工具。我国始终不断完善商业秘密法律制度和保护力度。但要看到,在商业秘密保护的基础理论研究、新型侵权行为的应对、商业秘密案件办理质效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同时,也应意识到商业秘密保护的核心不仅是对侵权行为的惩罚,更在于营造创新环境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未来,加强商业秘密司法保护,营造更加公平、透明、稳定、可预期的贸易投资环境和创新环境,促进创新主体充分利用国际国内创新资源,提高科技发展质效和国际化程度,仍是我国司法机关处理商业秘密纠纷的根本遵循。
注释
[1]Elizabeth A. Rowe & Sharon K. Sandeen, Trade Secret Law Cases and Materials,2(2ded., West 2017).
[2]《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rticle 39,WIPO,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305736, (accessed Jan 28, 2025).
[3]《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rticle 39, footnote 10,WIPO,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305736,(accessed Jan 28, 2025).
[4]《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第 18 章知识产权,载商务部网,https://gjs.mofcom.gov.cn/cms_files/oldfile//gjs/202101/20210114111537200.pdf,访问时间:2025年2月3日。
[5]《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第 18 章知识产权,载商务部网,https://gjs.mofcom.gov.cn/cms_files/oldfile//gjs/202101/20210114111537200.pdf,访问日期:2025年2月3日。
[6]《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第 18 章知识产权,载商务部网,https://gjs.mofcom.gov.cn/cms_files/oldfile//gjs/202101/20210114111537200.pdf,访问日期:2025年2月3日。
[7]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相互质证。对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需要出示的,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示。”
[8]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122条第2款:“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
[9]国务院知识产权办公会议办公室编:《知识产权法法规总汇》,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774页。
[10]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1款和第2款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的类型:“经营者不得采取下列手段侵犯商业秘密:(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得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违法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11]参见孔祥俊:《反不正当竞争法新原理(分论)》,法律出版社2019年3月第1版,第444页。
[12]参见陈雨禾等:《准确评价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三个方法》,载《检察日报》2024年12月20日第3版。
[13]孔祥俊:《商业秘密保护法原理与判例》,法律出版社2024年11月第1版,第234页。
[14]参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22)粤0115民初2627号民事判决书。
[15]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8页。
[16]王瑞贺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32-33页。
[17]参见孔祥俊:《商业秘密保护法原理与判例》,法律出版社2024年11月第1版,第237页。
[18]王瑞贺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32-33页。
[19]孔祥俊:《反不正当竞争法新原理(分论)》,法律出版社2019年3月第1版,第449页。
[2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被诉侵权人以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公认的商业道德的方式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所称的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21]商业道德是在市场竞争中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核心内容。在有公认的商业道德可依据时,应当依据公认的商业道德判断竞争行为的正当性,但在新产业新市场等缺乏公认商业道德的领域,裁判者需要依据法律精神、市场需要等确定可资遵循的市场道德准则,以此判断竞争行为的正当性。公认的商业道德对于市场竞争行为更多的是一种规范作用,裁判者确立的商业道德则是一种对市场竞争标准的形塑作用。
[22]《民法典》第509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23]《民法典》第558条规定:“债权债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等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旧物回收等义务。”
[24]参见黎华献:《商业秘密保护中默示保密义务研究》,载《中国法学》2024年第 4期,第141页。
[25]孔祥俊:《反不正当竞争法新原理(分论)》,法律出版社2019年3月第1版,第358页。
[26]《民法典》第1169条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27]2025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规定。
[28]王瑞贺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释义》,法治出版社2018年版,第31页。
[29]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课题组:《商业秘密司法保护规则研究》,《知识产权》2024年第10期,第40页。
[30]参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知民终282号民事判决书。
[3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1687号民事判决书。
[32]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0)京73民初1114号民事判决书。
[33]《全国首例以合理许可费确定损失数额的案件在津公开审理》,载金台资讯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8873634619768660&wfr=spider&for=pc,访问日期:2025年2月1日。
[34]林广海等:《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报》,2020年10月29日第7版。
[35]参见刘孔中等:《论商业秘密保护及其过度保护的问题》,《知识产权》2022年第5期,第78-82页。
[36]参见孔祥俊:《商业秘密保护法原理与判例》,法律出版社2024年11月第1版,第236页。
[37]林广海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法律适用》2021年第4期,第16页。
[3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26号民事判决书。
[39]参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6)沪73民初898号民事判决书。
[40]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541号民事判决书。
[41]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8)京73民终1249号民事判决书。
[4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621号民事判决书。
[43]参见中国社会科学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6年6月第7版,第1339页,。
[44]参见孔祥俊:《反不正当竞争法新原理(分论)》,法律出版社2019年3月第1版,第426页。
[4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5条,“商业秘密权利人提供证据证明被诉当事人的信息与其商业秘密相同或者实质相同且被诉当事人具有接触或者非法获取该商业秘密的条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或者已知事实以及日常生活经验,能够认定被诉当事人具有采取不正当手段的较大可能性,可以推定被诉当事人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事实成立,但被诉当事人能够证明其通过合法手段获得该信息的除外。”
[46]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知民终1590号民事判决书。
[4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知民终593号民事判决书。
[48]DIRECTIVE (EU) 2016/943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8 June 2016, on the protection of undisclosed know-how and business information (trade secrets) against their unlawful acquisition, use and disclosure, EUR-Lex,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16L0943, (accessed Feb 15, 2025).
[49]《Uniform Trade Secrets Act》, file:///C:/Users/Bing/Downloads/trade_secrets%20(2).pdf, (accessed Feb 15, 2025).
[50]DIRECTIVE (EU) 2016/943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8 June 2016, on the protection of undisclosed know-how and business information (trade secrets) against their unlawful acquisition, use and disclosure, EUR-Lex,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16L0943, (accessed Feb 15, 2025).
[51]参见(美)詹姆斯. 普利:《商业秘密:网络时代的资产管理》,刘芳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60-61页。
[52]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2278号民事判决书。
[53]崔星路:《德国商业秘密保护法学的学理启发》,《海峡法学》2023年第2期,第91页。
[54]U.S. Code § 1201 – Circumvention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systems,Cornell Law School,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17/1201, (accessed Feb 16, 2025).
[55]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三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
[56]参见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0民初788号民事判决书。
[57]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Information about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s China Initiative and a compilation of China-related prosecutions since 2018, Nov. 19, 2021, https://www.justice.gov/archives/nsd/information-about-department-justice-s-china-initiative-and-compilation-china-related. (accessed Oct, 20, 2024).
 合肥知识产权律师网
合肥知识产权律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