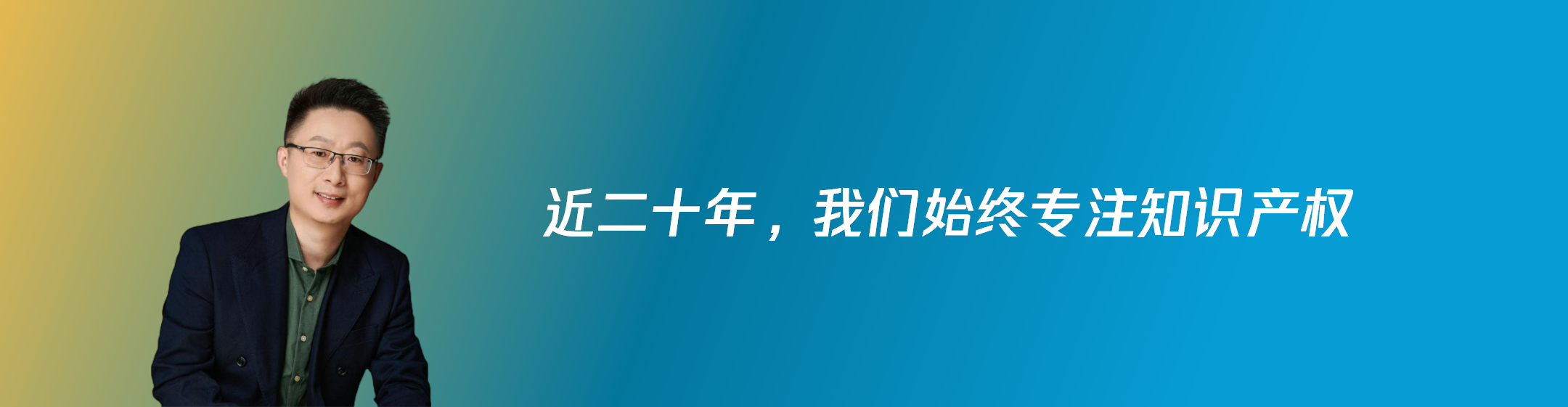作者:陈军、肖一波 天禾律师事务所
商标抢注行为指行为人明知他人在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已积累商誉,仍恶意抢先注册相同或近似商标以谋取不正当利益。此类行为侵害权利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竞争与商标管理秩序。司法实践中,对其能否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存在显著分歧:部分法院援引该法第二条认定此类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另一部分法院则认为应限于商标法救济路径。争议焦点集中于行为性质界定、法律适用顺位以及原则条款边界。本文通过剖析裁判案例,厘清裁判逻辑,探讨商标抢注行为在竞争法框架下的可规制性及适用要件,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一、实践中存在的行为类型
实践中,商标抢注行为存在多种行为类型,针对不同的行为类型,司法裁判情况亦存在较大差异。笔者试罗列归纳以下三种行为类型,即抢注商标后实际投入使用、抢注商标后滥用商标权以及单纯的商标抢注行为。对于抢注商标后实际使用行为,司法裁判争议较小,法院通常会结合商标抢注后的使用行为,综合认定其构成商标侵权。而对于并未实际投入使用的商标抢注行为及后续权利滥用行为能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司法裁判存在较大分歧。
(一)抢注商标后实际投入使用
该行为类型的典型模式为,商标抢注者抢注与在先权利人近似的商标后实际使用在其产品上,以攀附权利人商誉、获得竞争利益。例如碧然德有限公司、碧然德净水系统(上海)有限公司与上海康点实业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 (2017)沪0112民初26614号,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中,原告碧然德两公司自2008年起即在中国多地商场销售其BRITA品牌滤水壶,并以报刊、展览会、网络等方式对其品牌产品进行宣传。而被告康点公司自2012年至2016年期间,向国家商标局在多个商品及服务类别上申请包括“碧然德”“德碧然德”“BRITA”“DEBRITA”等注册商标,并且实际用于其网店、微信公众号宣传。
针对康点公司商标抢注及使用行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分别予以评价。判决认定其商标使用行为构成商标侵权,“被告明知原告享有‘BRITA’‘碧然德’等注册商标的专用权,未经原告权利人许可,在产品检测报告、产品包装盒及宣传册等所关联的商品上使用与原告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标识,并通过微信公众号及网络平台销售,其行为构成对原告上述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针对商标抢注行为与后续对于商标权的滥用行为,判决援引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认定其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抢注商标后滥用商标权
该行为类型的典型模式为,商标抢注者在该商标获得注册后倒打一耙,转而对权利人恶意发起投诉、商标异议、商标无效宣告、侵权诉讼等。例如上述碧然德有限公司、碧然德净水系统(上海)有限公司与上海康点实业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中,被告康点公司同时以自身抢注“德碧然德”商标作为引证商标针对同类别的原告“碧然德”注册商标请求宣告无效,以及对原告申请注册中的“碧然德”等商标提出异议。又如特拉克拉食品有限公司等与姚某等不正当竞争纠纷[[[] (2021)京73民终2185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中,原告特拉克拉公司在其牛肉及类似商品上的商标标识“TELARGRA”系普通商标,并未在中国进行商标注册。被告姚某及相关公司在特拉克拉公司实际使用“TELARGRA”商标后,向国家商标局申请“TELARGRA”等相关商标并成功核准注册。随后姚某及相关公司据此对特拉克拉公司在京东商城开设的店铺“特拉克拉旗舰店”进行了多次投诉,要求对涉案商品勒令下架,否则将司法处理。
针对姚某及相关公司商标抢注及后续的投诉行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其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并援引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原则性条款予以认定。判决指出,“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尚昇公司明知小牛约翰公司、特拉克拉公司对‘TELARGRA’标识享有在先权利并在先使用在生牛肉商品上,仍然利用小牛约翰公司、特拉克拉公司未及时注册商标的漏洞,将上述标识申请注册为商标及进行著作权登记,并以此作为权利基础针对特拉克拉公司在京东商城上销售的生牛肉类商品发起投诉,主观恶意明显。客观上,尚昇公司的被控投诉行为导致特拉克拉公司的涉案产品曾被下架,不仅直接影响了特拉克拉公司的经营收入,更干扰了对‘TELARGRA’标识享有在先权利的小牛约翰公司、特拉克拉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具有明显的不正当性。因此,尚昇公司的上述行为违背基本的诚信原则和商业道德,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损害了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属于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所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同时亦有法院认为商标抢注及后续商标权滥用行为不宜以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规制。例如北京畅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杭州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2024)浙民终1016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中,原告畅行公司注册有“嘀嗒”系列商标,在运输出行服务特别是网约车、顺风车领域已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被告杭州公司申请注册了大量“滴答”商标,将与“嘀嗒出行”相近似的文字“滴答出行”作为其公司网站名称,并针对畅行公司“嘀嗒”系列商标提出无效宣告请求。
针对杭州公司商标抢注及商标无效行为,人民法院认定其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所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判决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经营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且属于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及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规定之外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予以认定’由此可见,受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行为首先应当属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经营行为,发生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本案中,滴某公司申请注册‘滴答’系列商标及申请宣告畅某公司注册商标无效的行为,均属于向行政机关提出商标授权确权申请的行为,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制的生产经营行为。”
(三)单纯的商标抢注行为
该行为类型的典型模式为,商标抢注者批量持续性地抢注他人商标,从而使权利人负担极高的维权成本,阻碍权利人正常使用商业标识从事经营活动,进而达到削减权利人竞争利益的目的。例如西安某科技公司、西安某公司与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2022)陕知民终139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中,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了“元贝驾考”网站, 并申请登记以“元贝驾考”或“元贝”为名的数份软件著作权。后长期囤积商标的上海某公司在第42类注册 “元贝驾考”商标。西安某公司在从上海某公司受让取得“元贝驾考”商标及“元贝驾考宝典”应用软件,并授权其持股的西安某科技公司使用。西安某科技公司上线手机软件名称为“元贝驾考”,并投诉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商标侵权。该案中,上海某公司实施单纯的抢注行为,西安某公司、西安某科技公司受让该被抢注商标并滥用商标权。针对上海某公司的商标抢注行为,人民法院认定“涉案注册商标‘元贝’原注册人上海某公司的注册行为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具有复制、模仿他人商标、囤积商标进行不正当竞争或谋取非法利益的意图”,“受让的商标又属于以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商标,具有攀附他人商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明显意图,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由此可见,针对上海某公司的商标抢注行为,法院在反不正当竞争法范畴内予以负面评价,认定其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范畴。
又如某某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与沈某某因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 (2023)闽民终1048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中,沈某某与某某公司均系婚纱摄影行业经营者,在市场经营中存在竞争关系。某某公司的字号经过持续宣传和推广,在婚纱摄影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后沈某某在41类微缩摄影、摄影等服务上大量申请注册包含某某公司字号的商标,申请周期长达5年。国家知识产权局针对其所申请注册的若干商标作出的不予注册决定或无效裁定中指出,“沈某某的申请商标行为明显具有抄袭、摹仿他人商标的主观故意,不仅扰乱正常商标注册秩序,亦有损公平市场竞争秩序,违背了商标法关于禁止以欺骗手段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商标注册的立法精神”。人民法院亦认为“沈某某其申请注册众多包含某某文字商标的行为,抄袭、摹仿某某公司注册商标的主观恶意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扰乱了正常商标注册管理秩序,有损公平市场竞争秩序,损害了某某公司的合法权益,其行为不具有正当性”,因此认定其抢注行为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另有东莞市鸿兴食品有限公司、兴化市乐慧食品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 (2021)粤19民终2798号,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中,鸿兴公司在29、30类注册有多枚商标,经过长期经营宣传已积累良好商誉,其中一枚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评为中国驰名商标。后乐慧公司申请注册含鸿兴公司字号及“百俐”“味邻”“味邻皇冠”等系列商标。针对乐慧公司商标抢注行为,人民法院认定“乐慧公司作为同行竞争者,应当知道鸿兴公司的‘百利’系列注册商标或商品名称以及应当知道该系列商标或商品名称已使用在面包糠上。在此情况下,乐慧公司在面包糠上申请注册商标时不仅不予以避让,还将发音完全相同、字形高度近似的‘百俐’系列商标在面包糠上申请注册,甚至还申请注册与鸿兴公司‘百利’商标或商品名称完全相同的商标,明显具有攀附鸿兴公司知名度的恶意,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故意扰乱市场秩序,造成消费者对经营者主体的混淆,构成不正当竞争”。
与上述法院判例观点相反,对于单纯的商标抢注行为,部分法院认为不应援引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认定其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例如某某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某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 (2023)粤2071民初34905号,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中,某某熊公司注册有若干“某某熊”相关商标,经过长期持续的宣传和推广,某某熊公司的“某某熊”品牌在小家电行业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商标被认定为“广东省著名商标”、驰名商标。后某某知识产权代理公司以“某熊”“小某熊”或“小某熊+拼音”等为标识申请注册多达45枚商标。人民法院认定某某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商标申请注册行为实属商标恶意抢注申请行为,但认为其不构成不正当竞争,不宜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予以救济。该案生效判决指出,“第一,商标注册申请行为本身可以通过商标法相关条款予以行政救济……;第二,商标注册申请行为系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注册商标的行政行为,在没有注册后滥用商标权的行为的情况下,难以将单独的商标注册行为认定为生产经营行为,故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制的行为;第三,就在案证据而言……没有证据证明某甲公司、刘某使用了被诉核准注册的商标,被诉40多枚商标中存在权利冲突的商标在审查注册中已被驳回注册申请或决定不予注册,又或在获准注册后裁定宣告无效,刘某亦将相关核准注册的商标予以注销,某某熊电器公司的合法权益已得到相应的救济”。
又如金牌某公司等与高某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 (2024)浙民终894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中,人民法院认定“金某控股公司申请注册60余枚‘金牌’系列商标、品某电器公司申请注册3枚商标的行为属于向行政机关提出商标注册申请的行为,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制的生产经营行为。此外,对于申请注册商标侵害他人在先权利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设置了异议、评审和司法审查的救济程序,金某厨柜公司主张前述被诉行为构成抢注商标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但是商标的效力须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进行逐一审查判断,前述商标历经金某厨柜公司提起商标异议、无效宣告、商标复审、行政诉讼等程序,仍有20余枚商标处于有效状态,如果在商标民事侵权诉讼中将批量商标注册行为不加区分地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很可能与商标授权确权程序的处理结果产生冲突。考虑到纯粹商标注册行为的性质,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商标法尤其是商标授权确权程序之间的协调关系,本院认为不宜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对涉案商标注册行为进行规制”。
另有北京奕天世代商贸有限公司与湖南金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湖南金捷智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 (2019)闽02民初1502号,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中,奕天世代公司注册有“氣味圖書館”商标,经过其长期的销售、宣传与推广,该品牌已具备较大影响力,积累良好商誉。后金捷生物公司申请注册包括“气味博物馆”“气味情调家”等在内的商标300余件。人民法院认定“金捷生物公司注册商标数量达300余件,涉及‘气味博物馆’在内的大量商标标识和不同商品类别,可佐证金捷生物公司注册商标的行为并非出于经营需要,其无合理或正当理由注册并囤积大量商标,涉嫌侵犯不特定市场主体的权利,扰乱了正常的商标注册管理秩序”。但对于能否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人民法院指出,“在本案中可否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追究金捷生物公司的责任,还应审查金捷生物公司抢注、囤积商标的行为是否损害奕天世代公司的合法权益,即损害对象的特定化。本案中,与奕天世代公司合法权益相关的‘气味博物馆’系列商标已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准予注册,金捷生物公司合法注册取得‘气味博物馆’商标在其他核定商品或服务类别的专用权,其不构成对奕天世代公司涉案注册商标的抢注、抄袭,而奕天世代公司的合法权益不会因金捷生物公司抢注、囤积其他不特定权利人商标的行为而受到直接损害,也就是说奕天世代公司与金捷生物公司抢注、囤积他人商标的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在此情况下,奕天世代公司对金捷生物公司的该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具有适格性,不能以金捷生物公司损害其他不特定商标权利人的利益、有损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为由,主张金捷生物公司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所规制的不正当竞争”。
二、司法对商标抢注行为认定之顾虑
针对单纯的商标抢注行为,人民法院认定其是否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能否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予以规制时,存在较大争议。笔者试归纳人民法院持否定态度的理由如下。
(一)商标抢注行为并非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制的市场经营行为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该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而商标抢注行为本质上系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注册商标的行政行为。在没有注册后滥用商标权的行为的情况下,难以将单独的商标抢注行为认定为生产经营行为,故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制的行为。
(二)对于商标抢注行为的救济应围绕商标法规定展开
商标抢注行为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有违其他部门法程序安排。商标注册申请行为本身可以通过商标法相关条款予以异议、无效等行政救济,以上诸多行政救济途径属于法律赋予商业主体取得和维护其商标权的程序安排。针对以上商标局的异议、无效决定,权利人亦可提起商标行政诉讼,商标法已然充分保障了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通过行政以及司法手段维权的权利。因此,权利人应当首先在商标局行政阶段解决争议,并可就行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对他人抢注商标的行为商标法已经规定了较为全面的救济手段,无需通过其他诉讼途径主张权利。
(三)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系原则性规定,应审慎适用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作为该法的“一般条款”,其核心功能在于对法律未明确列举、但确属违反诚信原则和商业道德、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进行兜底性规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亦规定,经营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且属于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及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规定之外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予以认定。对于商标抢注行为,直接援引该条款予以规制应保持高度审慎,需满足司法解释规定的具体情形。原则性条款的适用具有补充性、谦抑性的特点,其本质是填补法律明文规定的“空白”。针对商标抢注行为,商标法已明确设立了异议、无效宣告等行政和司法救济途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亦详细列举了具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若绕过商标法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的具体规定,直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不仅可能架空商标法的专门制度设计,也违背了法律适用中“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基本原则。
三、对商标抢注行为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之必要性
商标抢注行为本身系以申请注册商标的行政行为形式达到不正当竞争的目的,因此不能仅凭行为外观认定其不属于市场经营行为。对于商标抢注行为的救济固然应当首先以商标法途径展开,然而现行商标法针对商标抢注行为的救济路径存在许多无法弥合的缺陷。商标抢注行为客观上侵害经营者利益、消费者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而商标法途径并不能对以上三元利益实现全面保护。因此对商标抢注行为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规制具有现实必要性。
(一)商标抢注行为属于市场经营行为范畴,且并非应容忍的商业风险
商标抢注行为虽然在外观上属于向行政机关申请注册商标的行政行为,但其本质上系以行政行为之名行市场竞争之实。商标抢注行为并非用于自身正常、合理使用,其目的在于攀附他人商誉或对他人竞争利益造成妨碍,从而获得相对竞争优势。对于市场经营行为应当采取更加实质性的解释,不能因商标抢注行为具有行政行为外观即忽视其市场竞争本质目的。
同时,商标抢注行为也并非应当容忍的商业风险。商业活动天然伴随风险,如市场波动、技术迭代或消费者偏好转移,此乃经营者应预见并应对之常态。然而,商标抢注行为系通过不正当手段将他人已在先使用并积累商誉的标识据为己有或设置障碍,本质是机会主义的侵权行为,而非市场竞争中可预期或应被动承受的“商业风险”。商标抢注行为以攫取他人商誉或阻碍竞争为目的,违背了商业活动应遵循的诚实信用基本原则。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要求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原则及公认的商业道德。商标抢注者明知他人在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具有相当影响力,仍恶意申请注册,明显构成对诚信义务的违背。
(二)针对商标抢注行为的商标法救济路径存在缺陷
我国商标法为对抗商标抢注行为提供了救济手段,主要体现为商标无效宣告程序与商标异议程序。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可针对商标抢注行为向国家知识产权局请求宣告该恶意注册商标无效或在抢注行为发生后提出商标异议。
然而,现行商标法救济路径存在显著局限。首先,除驰名商标外,对恶意注册的商标提起无效宣告请求,受五年除斥期间限制。若在先权利人未能在抢注商标核准注册之日起五年内发现或采取行动,将丧失无效宣告请求权。其次,商标异议程序虽然可用于在行为初期拦截抢注行为,但公告异议期仅三个月,且需权利人主动监测公告信息。商标抢注行为具有偶然性,且抢注者往往利用信息不对称实施抢注行为,导致权利人错失提起异议机会。再次,即便获得无效宣告,抢注者仍可就此裁定诉至法院,而行政诉讼程序时间拖沓两三年之久亦为常态。诉讼期间内,权利人同时面临市场被侵蚀、商誉受损等现实风险,抢注商标却处于有效状态,仍对权利人合法权益造成持续性损害。最后,在上述漫长的商标法维权周期内,权利人须针对每起抢注行为采取相关必要措施。维权行动势必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以及高昂的维权成本,同时对权利人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严重影响,导致权利人不堪重负。
(三)商标抢注行为导致三元竞争利益受损
反不正当竞争法体系形成发展过程中,其立法目标由保护经营者扩展为保护经营者、消费者、公共利益的三元叠加。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一条即规定,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本次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更加凸显了对消费者权益、公共利益的保护。
然而商标抢注行为不仅对权利人即经营者造成损害,同时侵蚀消费者及社会公共利益,导致三元叠加的竞争利益受损,这也是商标抢注行为得以受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制的实质要件。
第一,商标抢注行为侵害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商标抢注行为对权利人即经营者造成的损害最为直观。该损害一方面体现为权利人应对商标抢注行为的直接维权成本,即权利人面对商标抢注行为,被迫以不对等的行政、司法方式如提起商标异议、无效以及相应的行政诉讼所耗费的诸多成本。另一方面商标抢注行为使得权利人对其字号、商标等标识享有的权利陷入随时可能受到侵害的风险,使权利人无端暴露于商誉贬损、交易机会丧失、市场份额被挤占的侵害风险之中。第二,商标抢注行为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商标抢注行为往往针对其他经营者已具有一定影响力与商誉的商业标识。商标抢注行为使得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容易陷入混淆并由此引发一系列风险,即使商标抢注者抢注商标后未实际用于其商品,其所抢注商标与其他经营者标识同时存在的情况,仍会使消费者陷入选择混淆,进而减弱权利人商业标识(字号及商标)与其商品间所建立的联系。第三,商标抢注行为侵害社会公共利益。一方面,经营者利益、消费者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三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叠加、相互影响。经营者、消费者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正是市场竞争秩序扭曲的体现,因此商标抢注行为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另一方面,我国商标注册审查量非常大,此类不以使用为目的、大规模、长周期的抢注行为,将会给国家知识产权局平添大量商标审查工作量,扰乱正常的商标注册管理秩序,实质上损害了社会公众利益。
四、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商标抢注行为的适用条件
面对商标法保护缺位,三元竞争利益遭到损害的情形下,商标抢注者的行为亟需得到规制。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一部行为法,具有规制此类行为的天然属性。笔者认为在适用该法第二条一般性条款时,应作如下四方面的考量。
第一,商标抢注行为发生于生产经营活动之中,存在竞争关系。前已述及,商标抢注行为系以申请注册商标行政行为之名实现其不正当竞争目的之实,因此不能因其行政行为外观即认定其不属于生产经营活动。同样,对于竞争关系的判断也应当进行实质化的解读。这种竞争关系并不拘泥于直接同业竞争,在此可以对竞争关系进行更加实质化的解读。当抢注者与在先权利人处于相同或关联市场领域时,即可认为抢注者所实施行为具备竞争属性。位于相同、关联乃至上下游产业的抢注者实施商标抢注行为损害权利人利益,本质上均构成对权利人竞争优势的非法侵蚀,可以推定竞争关系存在。
第二,商标抢注行为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前所述,对于经营者、消费者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实质损害正是赋予适用该条款必要性的客观因素。商标抢注行为侵害消费者权益主要表现为选择混淆及由其衍生出的诸多风险。其对经营者权益的损害则可包括直接维权成本、商誉贬损、交易机会丧失等等。需注意的是,此时损害结果并不局限于实际损失,权利人“正当经营免受恶意干扰”的消极权益亦在竞争法益保护范围之内。商标抢注行为对于消费者、经营者权益的损害恰恰印证其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破坏。此外抢注行为将无端增添商标审查部门工作量,扰乱商标注册管理秩序。以上情形均属于认定商标抢注行为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客观依据。
第三,商标抢注行为违反法律和公认的商业道德。认定商标抢注行为违反商业道德,主要从商标抢注者具有主观恶意的角度进行分析。商标抢注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可见于其所实施的客观行为,在认定抢注者存在主观恶意时,可从多角度论证推定。若抢注者系权利人同业竞争者,则可认为抢注者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人在先权利的存在及使用情况,在此基础上实施抢注行为,难言善意。此外,若商标抢注者长期、批量抢注与权利人近似商标,以至于其注册的商标类别与数量明显超过其正常商业经营需求,亦可作为其具有不正当竞争主观恶意的佐证。因此针对单纯的商标抢注行为,认定行为人主观恶意的重点在于论证其是否明知权利人在先权益,以及其商标注册行为是否与其商业经营行为相匹配。
第四,商标抢注行为属于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及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规定之外的情形。如前所述,部分司法判决认为商标抢注行为属于违反商标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等规定的行为,不应再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提供救济,对此笔者以为不然。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第一条的目的在于防止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商标法对于同一法益进行重复保护。商标法规定商标注册申请人不得从事抢注行为,并赋予权利人提出异议、无效等救济手段。但在商标法规定范围内,无论异议或是无效,该救济手段仅仅针对被抢注商标具体的每一抢注结果,其结果仅仅是被抢注商标得不到注册或被无效。针对商标抢注行为,特别是同一主体以非正常方式大量申请、且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抢注行为,现行商标法无法能提供有效救济途径。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一部行为规制法,适用该法进行评价的对象是抢注行为本身,而非对所抢注商标效力有无的评价。因此从实质角度来看,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方面不会对权利人法益进行重复保护,另一方面也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第一条的立法目的。
五、结语
商标抢注行为在市场竞争中屡见不鲜,其对在先权利人、消费者以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不容小觑。实践表明,商标法虽提供异议、无效等救济路径,但其除斥期间限制、程序冗长及被动防御等局限,难以全面遏制恶意抢注。本文通过对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探讨了商标抢注行为在不同情形下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适用条件和边界。通过对商标抢注行为性质的分析,明确了其在特定条件下可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范围,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合肥知识产权律师网
合肥知识产权律师网